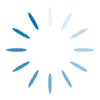八天前。
那天晚上的宴会,沉纪雯没有去。
换成几年前,她可能会抗议、耍点小性子,或者冷冷地问一句“到底在怕什么”。
但这次她没有。
她只是站在露台边,看着那辆黑色轿车驶出别墅大门,沿山道慢慢消失,尾灯一点点淡出雾气。
手里握着还没拆封的晚装耳环,指尖没有一丝动作。
她不是不明白。只是这次,她选择不问。
她知道欧氏持有的批文是什么,也知道政府手上已有数家地产商递交开发申请。
更知道现在欧氏面临的困境是什么。
单独那张旧纸,只会被人当成捷径。
第二天一早,沉纪雯照常跟欧丽华一起去了湾仔办公室,先帮秘书把那几份合同对了一遍,顺便看了最新的资金调度表。
秘书邮箱里有一封凌晨发来的项目简报,由中介机构转发,说是昨晚宴会后初步共识,由主办方提出。
她停顿了一下,眼神不动。
昨晚的宴会,母亲没有多说,她也没有多问。
她没有点开附件,只是把邮件归档,又继续处理下一封。
午休结束,她看到秘书正在会客厅处理今早送到的三张请柬,都是近一周的地产圈聚会。纸卡色泽鲜亮,字迹浮金,每一张都写着“敬请莅临”。
三张请柬上都有署名,名字不一,但落款的那些公司,她全记得。
她从小就记得。
记得有一位董事每年冬至都送礼来太平山,说是“顺便看望沉小姐”;
也记得每年生日前后,太平山总会收进来各式各样的花篮、名片和丝带包好的礼物,落款全是某某公司、某某太太,没人真提名字,只说“转交给沉小姐看看就好”。
只是以前母亲从不让她碰。
现在那些名字一个个浮出水面。
那晚,沉纪雯一个人在秘书办公室坐到深夜。
没开主灯,只打开那盏放在角落的立灯,把白天见过的那几张请柬重新找出来,细看了一遍署名、落款、主办单位,又打开秘书存放既往请柬的文件箱,翻出记忆中曾经送花来太平山的残页。
她最终把指尖落在一个名字上:方承屹。
二十六岁,方家三房次子。
祖父那一辈起家于旧立法局,家族至今在城中盘根错节,政商脉络深、动静都稳。
听说他那支脉系在方家里不算最硬,但这些年翻得极快。
他本人五年前从美国回港,入方家旗下资产公司做CEO,三年内完成四笔并购,没有一例留尾债。
宴会场里他的身边向来不缺人,从律师、主播到明星,出场从不空手。
但她知道,在那些拿来应付场面的人之下,他心里有一把最清楚的秤。
方承屹第一次找她说话,是她十四岁那年。
那是太平山每年例行的春酬。
她躲在花园角落看星星,风吹乱了头发,一身天蓝色纱裙,像是还没从学生制服里完全抽身。
他递给她一杯水,说:“你是不是觉得里面太吵?”
她没接,只是点头。
他也没多说,笑了一下,转身走回人群。
后来几年,她在无数个场合与他擦肩。
每一次他身边都有不同女伴,但每一次,总会绕过来和她打一句招呼。
“沉小姐最近在伦敦念书?”
“欧太今天没来?”
“你换发型了,挺好。”
他不是执着,他只是记得。
并且总在适当的时候,让她知道他还记得。
她十六岁那年,有一天太平山收到一对方家送来的南洋珠耳钉,说是方承屹从新加坡带回的,收件人是沉纪雯。
欧丽华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,只留了一句:“小姑娘不懂这些,以后别再破费了。”
那之后方承屹不再表露太多。
但每次宴会上碰到,依然会在她身边站定,闲话三句,从不多说。
沉纪雯从不觉得自己特别。
但在这个世界,有些名字值钱,不是因为你是谁。
她是欧丽华的女儿,是那栋太平山别墅里长大的沉纪雯。
哪怕现在形势如此,那几个字说出来,在商界依旧足以换来一次见面,一次试探。
她清楚,自己能带进会客室的东西,远不止一张名片。
她打定主意后,次日拨通了那个号码。
干诺道中三十八楼。
清晨光线打在会议室的胡桃木桌面上,一盏落地灯没关,窗边帘子也没拉,空气里只有纸张翻动声。
方承屹正看一份基金结构的调整方案。
页面摊在他桌面,左边一行数字用红笔划了记号。
秘书敲门进来,站在他身侧低声道:“刚有个电话打进来,说是想约您见面。”
他没有抬头,用红笔又划了一条线:“谁?”
“一位女士,说叫沉纪雯。”
他手指停了一下,翻页的动作轻得几乎无声。
“对方没说具体什么事。我说您这个月已经排满,原本以为就这样了,但她又重复了一遍,说‘你告诉他,是沉纪雯。’”
方承屹这才抬头,看了秘书一眼。
指尖缓缓从页面滑开,盖住红笔线条。
“明天下午三点,把明发城那场协调会往后挪。”
秘书有些意外地确认:“三点?”
“对。”
他语气不重,没再追问,也没要求多报行程。只是重新看向手里的文件,把那张红线页抽出,在桌上放平。
“把这份重排一下,调整完先发技术部,再发二组,我明早批。”
秘书点头,退了出去。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